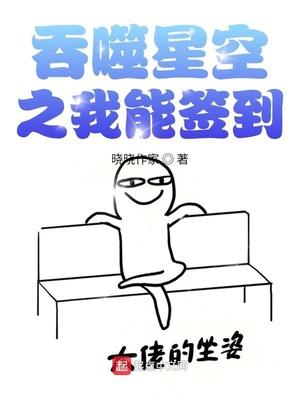言情阁>窈窈不相思 > 第286章 两小无猜(第2页)
第286章 两小无猜(第2页)
“你我之间,不必这么生分。”
“无论你遇上了什么事情,大事也好,小事也罢,都无所谓。只要你想得到我,就尽管差遣我便是了。”
“哪怕,什么事情也没有,你也可以叫我。我会一直等你的消息的。”
他终于苦笑着将她应下。
真庆幸,此时此刻,萧子窈依旧不在。
如此,她便看不见他的模样了。
夏一杰于是抬起头来。
传达室内,一扇窗子忽然被风吹开,那溅了油漆的白玻璃便一下子打了过来,又映出他的影子,施施然的,正好一片油漆挡在他眉眼的位置,像蒙上眼睛的死者,却是死不瞑目的。
不是不情愿,不是不甘心。
只是,不敢,而已。
如是而已。
“——子窈,今天天气有点冷,你就在家里等我,我很快就到。”
话毕,他便挂断了电话,快步走出门去。
其实,倘若较起真来、细细的算上一算,从军营到煤渣胡同,根本远远要比他到凤凰栖路来得更快。
却奈何他总也偏心,爱与不爱,都很明明。
更何况,有些祸事,本也不是他有意想要沾染的。
分明是他倒霉、是他受害!
——夏一杰只在心下这般想到。
他实在不敢说出口。
因着那宽慰不像宽慰,反倒像是自欺欺人,也许可以骗得过萧子窈罢,偏偏他却始终不忍。
他于是走得很急,只将车子一刻不停的打起火来,卫兵见此,还以为他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在身,便立刻放行了。
“夏副官你好,我要例行登记你的出入时间——请问你是被沈军长安排了工作吗?”
夏一杰于是想也不想,只管说道:“不是——但是,比那个更重要。”
萧子窈着实有些不敢置信。
那法兰西会所名字起得倒是洋气,可说穿了,到底还是个寻欢作乐的地方。
日本人学习洋人的包装之法,只管将一个新时代的窑子捧为欢乐场,如此,那里头的姑娘便不再是人了——不是人,却是银元、是物件,倘若当真有人想从中逃出生天,那她大约非要被剥下一层人皮不可。
她想不出小金铃走得掉的道理。
窑姐儿的卖身契都不便宜,有些个姑娘又是被老鸨一个卖给另一个的,中间更要算上添头,非但如此,人越红的、还越贵,一张契书能顶三间铺子都是常事,小金铃既是法兰西会所的头牌,想来,那边的东家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她去。
萧子窈只在心下粗算着,面色却愈的沉重起来。
“那,郝姨,你可有问清楚,小金铃姑娘辞职后去了哪里?”
郝姨微微颔,有些失落。
“回夫人,我已问过了,可是那会所里的人口风都很紧,无论是经理还是门童,不管我怎么问,他们都说不清楚、不知道,反反复复就只说一句,说小金铃姑娘已经攀上高枝飞走了,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
“攀高枝?说得倒是好听!”
萧子窈冷哧一声,“要是小金铃当真攀上了高枝,那我反倒放心了,她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女孩子,有人替她赎身总是好的。更何况,能买得起她的人非富即贵,不至于以后短了她的吃穿。但岳安城来来回回就那几个有钱人,小金铃若是被其中的哪一个赎走了,我总能听到些风声!可日子过去了这么久,我却根本不曾听说过有谁养了外室或娶了妾,只怕是小金铃姑娘出了事,这些话全当是说来打我们的!”
她话音方落,郝姨立刻心领神会,于是面色一紧,忙不迭知会道:“那、那要不然,您让沈军长帮您查查看?”
萧子窈冷然拂袖。
上一回,小金铃正好触了沈要的霉头,只怕要将人杀了还不够呢,眼下,她又哪里还敢将此事说与那疯狗听去!
“他最近太忙了,脱不开身,我自己再去想想办法。”
万不得已,她只得这般安慰起郝姨来,“郝姨,钱你照常收下。只不过,这些事情,千万不要说给沈要听,免得打扰到他,知道了吗?”
郝姨一瞬了然。
她实在是再规矩不过的下人了,同她讲话,从来不必说得太多或太深,因着她总会有自己的分辨,既能保命、也能长命。
萧子窈于是放下心来,后又歇了片刻,忽然说道:“郝姨,之前夏一杰第一次来家里做客时,曾带来过一张茂合戏院糯米红豆沙的方子,你可还记着吗?”
“记着呢!”
郝姨翻篇一笑,仿佛方才的事情都做假,道,“莫不是夫人嘴馋了,想吃?”
“——我打算请客人来吃。”
说罢,她便站起身来,只管往那搁着电话机的小几上一靠,好像个弱柳扶风的林妹妹似的,然后转着转盘拨了号,没等多久、便接上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