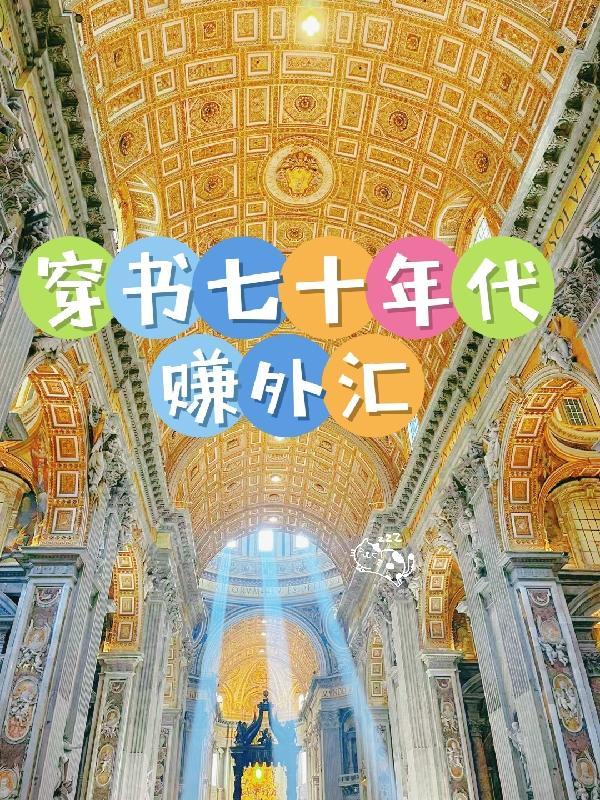言情阁>逐出侯府!弃女竟成了团宠太孙妃 > 第73章 上门逼迫(第1页)
第73章 上门逼迫(第1页)
阮桃还是那副做派,进了梅宅,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脸色虽不阴沉,却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这次上门好歹提了两包点心。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家里都闹翻天了,三弟妹好清闲。”
阮桃第一句话里就带着讥讽,实在是梅氏坐在廊下做绣活的样子太悠闲了。
“大姑奶奶此话怎讲?我做绣活是为了养家糊口,哪来的清闲?”
阮桃没想到梅氏会反驳,气哼哼说道。
“阮珂那么小,你就让他上街去玩耍,这次是没出事,要是出了事,老三回来,你怎么跟老三交代?”
梅氏心里已经懊恼,当时要是不同意阮珂跟着青萝出门,也就不会有这事。这会儿听阮桃这么说,更加自责。
“老二什么性子你也清楚,他决计不会做出这种事。阮珂是他亲侄子,他怎么舍得?都是你那本家哥哥干的好事,逼着老二,还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他也是为了保命,迫不得已。要怪,只能怪你们把你本家哥哥撵出去了,导致他怀恨在心。
他们本来要杀了阮珂,还是老二说了好话,那些人才没有伤到阮珂,老二虽然参与了,但也是有功劳的。你去衙门把案子撤了,说到底咱们还是一家人。老二有个好歹,你们也不好看。说出去还是你们害了老二。”
梅氏愣愣看着阮桃,什么叫他们害了阮柏?阮珂是没出事,可是青萝直到现在还昏迷不醒,昨后半夜起了高热,满嘴胡话,她都要吓死了。
现在阮桃来让她撤案,这话阮桃怎么说的出口?梅氏嘴都哆嗦起来,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当初把你们除族,都是族里几个族叔强压,娘怎么抗的过那几个老顽固?反正老三的事已经这样,娘的意思,过两年,老三的事没人谈论了,你们还回去。你想啊,青萝和小珂没了侯府做依靠,以后说亲都要矮一大截。你就算不为你自己打算,也得为两个孩子打算。这时候要是你不撤案,不帮着老二,往后你们还有什么脸回府?”
破天荒的,梅氏没有把阮桃的话听进去,这是画大饼呢,今天画一个,明天画一个。哦,阮柏绑架阮珂,伤了青萝,这会儿阮桃上门来说都是一家人了,呸。
阮桃见梅氏不说话,还以为梅氏被说动了。继续说。
“青萝马上到了说亲的年纪。有侯府千金的身份,总是好的,说亲时候人家也高看一眼。你要知道,犯官之女是找不到好人家的。”
一旁伺候的郑妈妈气的不行,既替自家小姐叫屈,又担忧梅氏真答应下来。急忙抛下规矩插嘴。
“要说这世上,还真是什么人都有。有些人为了保护别人,生死不顾,就像我家小姐,为了救少爷,连命都不要了,两条胳膊生生被砍了那么深的口子,双腿都快废了,就这会儿还躺在床上没醒过来呢。
可有些人,丧尽天良,什么被逼无奈?什么刀架在脖子上?他被逼无奈就绑架我们家少爷?就要砍死我家小姐?他欠一屁股赌债就要祸害我们家?真不知道还有没有天理了?老天爷瞎了眼让这种祸害活在世上,怎么不早点收了去。”
“你——”
阮桃被郑妈妈怼的脸红脖子粗,指着郑妈妈怒吼。
“你算什么东西,主子说话哪有你一个狗奴才插嘴的份儿?给我掌嘴。”
“谁敢动手?我家小姐说了,这是梅宅,不是阮家,更不是裴家。阮大姑奶奶想耍威风,麻烦你回自己家。我们爷被除族了,不是你们阮家人。”
“你——贱婢。给我打。”
“不准打我妈妈,不准打我家人。你走,不要你来我家。”
阮珂紧握拳头,涨红了脸冲着阮桃怒吼。
“他绑架我,还是我的错?我没被绑架走那是我姐姐拼命救了我,那是碰巧遇到了凌王世子。想让我们撤案,没门。”
阮珂就差挥拳头和阮桃打架了,梅氏没有劝阻儿子,儿子说的对。她担心阮桃再次打儿子,站起来挡在儿子身前。
“阮大姑奶奶请回吧,案子我们不撤,衙门该怎么判就怎么判,他绑架我儿子,打伤我女儿,我,我不撤案。”
“你——梅若曦,你可想清楚,不撤案,你们这辈子都别回侯府。阮青萝和阮珂就顶着犯官儿女的名号,一辈子也找不到好人家。”
梅氏泪流满面。阮珂挥着拳头。
“不撤案,他砍伤我姐姐,我们绝不撤案。我们不回侯府,我们自己过自己的。”
冬麦气冲冲从东厢房出来,双手叉腰站在当院,冲着堂屋怒吼。
“还想来我们家逞威风?还想打我们?还想逼我们撤案?呸!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我家小姐给你们留脸面,你们倒给脸不要脸了。我家小姐醒了,小姐说,阮大姑奶奶要不走,我们就抬着小姐去衙门,让京城的百姓们都看看,阮二爷是怎么欺负我们的。小姐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这还不够吗?还有脸来我们家,呸——真恶心!”
阮桃的脸瞬间变白,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也敢这般指责她,也敢在她面前大喊大叫?反了!反了!
“去,快去,给我按在地上打,狠狠打。”
冬麦扭头对长生说。
“长生,去街上大声吆喝,就说阮家欺人太甚,绑架少爷,砍伤小姐,还想逼迫咱们家撤案。满大街吆喝,咱们关帝街太小,去西大街吆喝,让全京城的人都听听。”
“贱婢,你敢——”
阮桃气得从椅子上站起来,抖着手指着冬麦,大口大口喘粗气。
“梅若曦,你怎么当的家?一个一个贱婢都爬到你头上了。赶紧把他们给我打杀了。”
“呸,不要脸。来我们家耍威风了,我们不怕。长生,拿个铜盆,敲起来吆喝。小姐说,出了事有她呢。”
阮珂拿着铜盆和棒槌要跑出去,阮桃破口大骂。
“把他给我抓回来,快点——”
此时的阮桃面目狰狞,像个疯婆子。
“谁敢——”
声音从东厢房门口传来,很弱,但足以震慑阮桃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