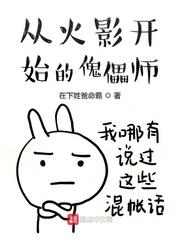言情阁>折竹碎玉 > 第189章(第1页)
第189章(第1页)
萧窈点头,鬓上的凤凰衔珠步摇随之晃动:“你真该看看萧巍的脸色。”
崔循了然道:“可以想见。”
“他如今在建邺,与江夏往来通信多有不便,桓维又无意鼎力相助,便是再怎么不甘,眼下也只能忍气吞声。”萧窈稍稍正了神色,“但我观他态度言辞,江夏那边恐怕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但萧窈原本也没指望,仅凭立储便一劳永逸。
说是“幽会”,实则却聊起这些来。
崔循并未打断,只拢了她的手,安静听着。
待萧窈大略讲过自己的打算,微微颔首,道了声“不错”。指尖摩挲着她纤细的手腕,低声问:“想这些,不会厌烦吗?”
“有时会,”萧窈顿了顿,坦然而认真道,“但我总要做些什么。”
从前争吵时,崔循曾咄咄相逼,告诉她不独士族藏污纳垢,皇室亦如此。
萧窈无法反驳。
因就连她给了颇多照拂的寒门学子,也并非个个都如管越溪、杨鸿光这般上进。甚至有人被纨绔带着胡来,出入秦楼楚馆,为他们代写功课,逢迎奉承,低声下气讨好。
明明当初皆是尧祭酒亲眼看过,精挑细选的人,却也会如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萧窈自学宫属官递来的奏疏得知此事,初时愤怒,渐渐却觉出些难过。
她独自枯坐许久,最后叫人传了谢昭来。
虽说今时不同往日,谢昭早已不再是从前那个闲散无事的协律郎,但他身上到底还担着学宫司业一职。
学宫递来这封奏疏,是因此事牵涉几位世家子弟,属官们不敢贸然处置,故而特地请示上意。
萧窈将这封奏疏给了谢昭,叫他查明原委,再着人按规矩责罚。该罚戒尺的罚戒尺,该抄书的抄书,不得有任何偏颇容情之处。
谢昭没什么避讳,立时应了。
却没告退,倒是看着她欲言又止。
萧窈问他缘由,谢昭玩笑一般开口道:“臣原以为,公主会叫人将他们都撵了,免得留着碍眼。”
萧窈没好气瞥他一眼。想了想,又的确像自己早几年能做出来的事情,便无奈叹道:“我倒是想。”
谢昭又道:“公主若心中难过……”
萧窈没叫他将话说完,面无表情道:“召你来时,已经难过完了。”
难过归难过,事情也总是要做的。
谢昭像是头回认识她一样,怔了片刻,随后收敛了笑意,垂首赔礼:“是臣看轻了公主。”
萧窈懒得计较,抬手打发他办事去。
她其实能猜到谢昭的心思,也明白崔循的用意。
在他们眼中,她就像是枝合该养在温房中的花,天真到受不得日晒雨淋,狂风一吹便要折了。
但不是这样的。
“我已知世上事并不非黑即白,也难一概而论。士族风气糜烂,萧氏谈不上干净,就连寒门子弟也泥沙俱下……”
萧窈声音很轻,几乎融入夜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