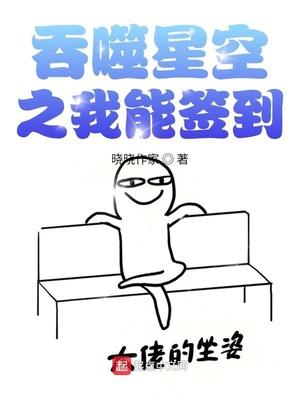言情阁>幻海寻渚 > 三十四 复仇(第1页)
三十四 复仇(第1页)
弓先生皮笑肉不笑道“我今天心情不错,诸位还有谁愿意和我切磋的,尽管上来”,一双冷眼闪着寒光,朝众人逼视。座下本在喧闹,被他厉目一逼,立刻鸦雀无声,竟无人敢于应战。
弓先生冷笑一声,正要收剑,突然一个青年纵上武台,叫道“我来朝你讨教几招如何?”,正是雷秉。
众人见是个陌生的毛头小子,都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替他捏了把汗,弓先生也稍稍一愣,旋即微笑道“好,你报上名来!”。
雷秉不答,冷笑反问道“弓先生,你可曾到过川北猿臂镇?”。弓先生顿时笑意全无,右手不自觉握住了长剑。
雷秉见他并不否认,欣慰之下仰天长笑,一鼓作气道“你本姓张,不姓弓;本来使钩,不用剑。你还有个使长枪的兄弟。你二人并称秦岭二张,受泸洲城于长锦买凶,在川北猿臂镇做过一桩惨案,是不是?”。
弓先生面色惨白“你是青龙会的人?
雷秉眼里要喷出火来,狞笑道“在下姓雷,正是你们当日漏杀之人。苍天有眼,叫你今日撞在我手上,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早难按捺,拔剑冲出。弓先生重重“哼”了一声,提剑迎上。
这是血仇相见,分外眼红。雷秉一柄利剑似狂风骤雨般狂刺,对方狠,他更狠,对方快,他更快。不出十数招,“扑哧”一声,一剑刺透了弓先生左肩,众人又是惊讶,又是痛快,哄然叫道“好!”。
雷秉手刃仇人,快意无比,狠狠笑道“爷爷今日要把你刺成一身的血窟窿方休!”,又是一剑,洞穿了对方肩臂,拣的都是不致命的部位。
弓先生右臂中剑,长剑铮地落地,双臂下垂,两股鲜血自右肩淌下,淋湿了衣裤,裤管都粘在了腿上。脸上再无高深的冷傲,取而代之的全是惧色和哀求,突然间双膝一软,跪了下来。
雷秉忆起父母兄长惨死之状,顿时心肠如铁般坚硬,哪里管他求饶,哈哈冷笑声中,正要再给他添个血窟窿,突然一人仗剑挡来,把弓先生护在身后,竟是苗秀。
雷秉双目圆睁,厉声呵道“你要作甚?快滚开!”。苗秀道“雷少侠,你要找他寻仇,等他出了庄子再说!”。
雷秉怒道“此人乃是云贵川恶贯满盈的悍匪恶贼,武林和朝廷都欲杀之后快。你不分好歹,竟要保他?”。
苗秀摇头道“我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和你有什么过节。他是王老侠的门客,只要还在‘伏枥庄’一天,我作为西厅主持,不能眼睁睁见他丧命。”
雷秉仰天一笑,切齿道“此人和我是不共戴天的血仇,谁敢挡我,我就杀谁!”,不理苗秀,一剑径刺弓先生。
苗秀挥剑一挡,雷秉怒起,剑势陡然一转,一剑斜拖,转瞬间从苗秀右腿根划到左乳,剌出两尺长的一道浅口。四座均是大惊失色,心想这一剑要是加了半分力,苗爷立刻便是开肠破肚。
雷秉怒喝道“你这两招三脚猫的功夫,岂能拦我?快闪开”。苗秀也是骇然失色,仍是不走,叫道“弓先生,快走!”。弓先生二话不说,站起往外便冲。他双足未伤,最后一丝活命的希望之下,窜得比兔子还快。
雷秉要追,却又给苗秀一拦,狂怒之下,再难按捺,一剑便要将他刺倒。突然如洪钟般的一声“剑下留人!”。
一个大身影扑了出来,将弓先生一拦,两只大手一抄,竟将他活生生捉了起来,往前连冲数步,喝道“回去罢!”,猛地一掷,将弓先生扔出三丈开外,照雷秉头顶坠下。雷秉在他摔死之前,一剑刺穿了他的胸膛,扑撒了满面的血雨。
雷秉快意长啸,再定睛去看那人,只见他足近六尺之高,身材壮硕,似铁塔一般敦实,须皆白,面色却红润,双目闪着精光,哪里像是近八十的高龄?正是王凌风了。众人都叫了一声“王老侠!”。
王凌风点了点头,突把苗秀一瞧,正色道“苗先生,你今个儿算是真糊涂!这姓弓的既然是官府都要缉拿的恶徒,人人可擒而诛之。为什么不能在这庄子里动手?难不成这‘伏枥庄’竟是法外之地?”。
苗秀低头道“王老侠教训的是!”。
王凌风不理他,又把雷秉一瞧,一拱手,道“这位就是雷少侠罢?老夫名叫王凌风,‘伏枥庄’的庄主”。
他虽然声名显赫,自报姓名之时说“名叫”,却不说“正是”,足见为人谦逊,并不以盛名自居。雷秉听得真切,当即更添了几分敬意。
这边西厅事毕,王凌风将雷秉引至书房,说道“昨日是亡妻忌日,路途不近,便在家祠歇了一晚。怠慢了雷少侠,请你见谅”。
他言语谦卑,雷秉反倒窘,连忙唯诺客套。王采乔兑现了诺言,果然捧着雪茶上来。雷秉喝了两口,味道平淡,不合胃口,但也只说好喝,王采乔当了真,接二连三又沏了好几杯来。
王凌风把她一瞧,微笑道“傻丫头,别人家请客灌客人酒,你却来灌茶!”。王采乔方才作罢。雷秉打趣道“王大姐好心肠,怕我皮肉浑浊,一杯半杯的沁不进去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