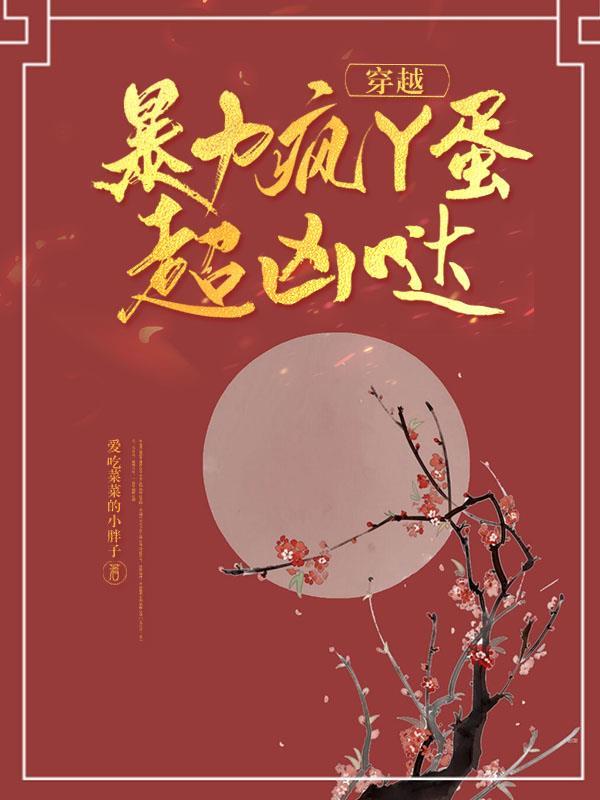言情阁>金丝笼牡丹 > 第110章 他打我了(第2页)
第110章 他打我了(第2页)
被母亲这样一哄,婠婠突然就压抑不住了自己的心情,呜呜咽咽地一下子被激出了眼泪,好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其实她不想让母亲担心自己,更何况如今的境地也是她自己选择的结果,她更耻于让母亲看见自己的失意憔悴,会让她感到羞耻。
她哭花了妆容,月桂端来一盆热水,绞干了手帕给她擦脸。热水氤氲着,似是唤醒了婠婠的一点神智。
“他打我了。”
她低声道。说罢又拾起了盆中的手巾覆在面上,不想去回想昨夜的事情。
此话一出,太后等人的面上俱是勃然大变。
“打你?他敢打你?他打你哪了?!要紧吗?良心被狗吃了的下作娼妇养的畜生,他怎么敢对你动手?真当我已经死了——”
云芝立马扯住了太后的衣袖,疾声规劝:“太后这话可轻易说不得!”
一则是如今人家已登大宝为天下至尊,二则殿内还有个不明白晏珽宗身世的华夫人在……
果不其然,听到太后骂当今皇帝是“娼妇生养的”时,华夫人的目光变得敏锐而疑惑,神色迟疑。可是她更在乎婠婠,于是也没有在这个关口纠结这句话的意义。
她拉起婠婠带她进了内殿,动手欲解下婠婠的衣裙检查她的身体。
婠婠不想被人看,还反被她们一起说了一通。
原本呢,不管是宫中还是宫外的世家大族里,几乎都有样不成文的规矩:长辈们身边得脸的奴才是比小一辈的主子要受人尊敬的。
甚至即便是宫里,好多帝姬都不敢和教养嬷嬷、乳母们顶嘴,宣扬出去了,皇后嫡母也只有一句话“你年纪轻,原只有姆妈嬷嬷们说你教导你规矩、没有你做女孩儿整天想着拌嘴不服管教的”。
于是她只得无语地抿着唇,轻轻抬起了头,由着乳母解下她的衣衫。
带着精致刺绣的衣裙一件件剥落,柔美身躯上斑驳的欢痕也暴露无遗。
她平素是喜洁的,可是今日起身时实在是累得不得了,所以还并未清洗过身体上昨夜纵欲后的痕迹。比起被自幼照顾自己的乳母嬷嬷们看见她赤|身|裸|体的私密模样,她更排斥被晏珽宗指派来的那些嬷嬷宫女们看见,也就不想让她们服侍。
太后连忙命人取了热水来准备服侍婠婠清洗。
她们以为婠婠说得被晏珽宗打了,若不是被他扇了耳光,那也是被他拳打脚踢地虐待过了,所以急急忙忙地去寻婠婠身上的伤口,可看见的确实一片情事中啃咬吮吸出来的斑驳痕迹。
即便是这样,布在一片凝白雪肤之上,犹如冰雪中的污浊斑点,看得人触目惊心。
月桂松了口气:“原来他倒没真跟您动手。”
是行房的时候过于放纵肆意些罢了。
华夫人却不赞成。
她利索地搀扶着婠婠进了浴盆,拿手巾擦着婠婠的锁骨,回头恨恨地道:“不是动了手,可是却比打了人折腾得我们殿下还狠。想是他馋死了,八百辈子没沾过女人的身!”
“殿下,他岂敢这样待您啊?他岂敢!当日求娶时,他和太后娘娘又是如何赌咒誓说得天一样好听。说什么,若是娶了您回去做太子妃皇后,必是爱如眼珠心肝至宝得疼着,天下万般珍宝都奉与您享用。这才几日?他就翻脸不认人?仗着得了手过足了瘾,便想将我们殿下丢到一边去了吗?”
太后紧皱着眉,神容严肃哀愁:“如今他是天下共主,四海八荒都是脚下凡泥,还有什么是他不能的?自然是想哪般行事就哪般行事了。”
昔日的帝姬,今朝也不过是他胯|下|泄|欲的玩|物罢了。
云芝和月桂恨恨地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可也想不出个什么主意来。
沐浴毕,婠婠虚脱地躺在母亲寝宫偏殿的床上不想动弹,华夫人取了一堆的香膏药粉来给婠婠处理身上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伤口,以指腹为她轻轻晕开药膏,细心涂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