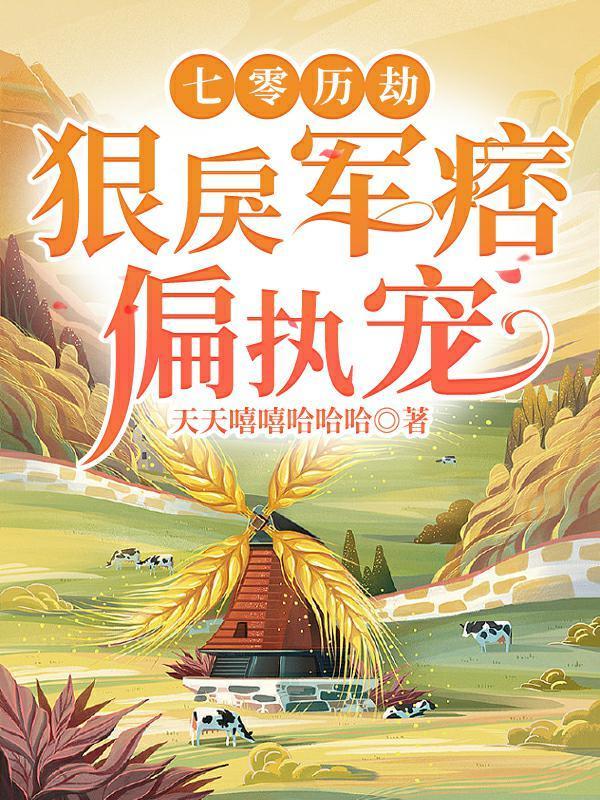言情阁>纪伊陆瑾深 > 第274章 爱与恨的身不由己(第3页)
第274章 爱与恨的身不由己(第3页)
“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在烟城。”她仔仔细细盯着陆淮康。
“叶家是混生意场的,隔行如隔山,你父亲案子的来龙去脉,柏南知道什么?”陆淮康面不改色,“你父亲贪污,包情人,勾结医疗公司滥用职权,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纪伊看着他,“父亲自杀那天,联系过您吗。”
“联系了。”他一半真话,一半假话,“我开会,秘书接听的。会议结束,秘书忙公事,没汇报,直到下班,我得知衡波自杀了。”
纪伊眼眸黯了黯。
“明天是衡波的忌日吧。”陆淮康翻日历,“去陵园扫墓吗?”
“哥哥有应酬,后天陪我去。”她越攥,越用力,“陵园在梅花山,初夏风景好,您登山散散心吗?顺便祭拜父亲,叙一叙旧。”
陆淮康拨弄着茶杯盖,“你们去吧,我在家休息。”
她仅存的期待,熄灭了。
其实,陆淮康夫妇上一炷香,在墓碑前掏心掏肺的鞠一躬,她也知足了。
哪怕,一句‘伊儿,对不起。’;或是一句‘陆叔叔有苦衷,你原谅我,原谅陆家。’
再不济,脸上闪过一丁点儿愧疚,一丁点儿向她坦白真相的犹豫,她也会不忍,会心软。
偏偏,陆淮康还在欺瞒。
纪衡波有罪,无辜的女儿、病入膏肓的妻子,不配得到一句对不起吗。
纪伊浑浑噩噩回到卧室。
亮着灯。
昏昧的橘黄。
窗台上焚了安眠的熏香。
竹海栀子。
纪伊喜欢栀子。
陆瑾深喜欢竹海的味道。
融合一起调制了一款。
“和父亲聊什么了?”他不甚在意地翻书,“在书房四十分钟。”
纪伊坐在床边,有一下没一下地梳头发,“聊你的糗事。”
他撩眼皮,“拖我下水是吧?你糗事多,我一件没有。”
陆瑾深洗了澡,短发潮漉漉的,前面的略长,垂散在额头,后脑勺的寸薄、凌厉,衣襟敞开,胸膛袒露,半倚半躺的姿势,腹部窝着,挤出一条深邃的沟壑。
勃发的肌肉,若隐若现的粗硬毛发。
欲而性感。
这样的男人,是没什么糗事的。
哪里出糗呢。
勾女孩,勾一个,成功一个;不缺钱,不缺爱,不缺地位,一辈子吃过最大的苦,是三十岁这年,爱与恨的身不由己。
“叶柏南送你的钻戒呢。”陆瑾深忽然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