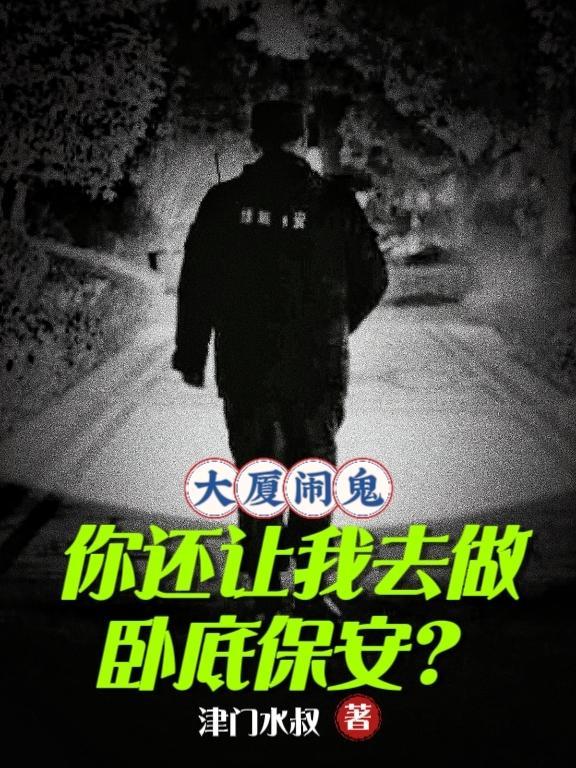言情阁>昼夜撩火 > 第八十三章 改口费(第2页)
第八十三章 改口费(第2页)
徐沉渊挣脱开她的手,救了她是一点儿没伤着,不了解就给他安这么个理由,他冤不冤。
她趴他身上,真是不小心看到,某人连内*都不穿,就粘了朵小花就出门,她现在要是敢这样搞,他怆死她。
他沉静如墨的眼眸寒涔涔,“没良心,松手。”
“凭什么?”温桥跟八爪鱼似的黏他身上,“我就不松。”
徐沉渊似想到什么,“不松就丢掉。”
她云里雾里,“丢什么?”
他攥紧她玉腕,拽她去衣帽间,跟拉滑轮胎似的被他拖着走,“干什么?”
徐沉渊松手,没说话。
衣帽间里一阵阵阴风飒飒飘过。
他沉声,“取出来。”
温桥推开衣柜门,那一排是挂睡衣的,她蹲下,身后荷叶裙摆垂落在木质地板上,手抖跟筋膜枪似的,从最底下掏出一盒子。
她蹲地上捂脸,“你怎么知道?”
“也是我的衣帽间。”徐沉渊神色淡漠。
他不确定,纯靠猜,一个人的习惯真没那么容易改掉,勾了勾唇弯腰拾起盒子往外走。
小样儿。
她提醒,“你还剩最后一个问题了。”
徐沉渊握住盒子的食指慵懒地轻敲两下,轻声嗯。
须臾,温桥下楼吃饭,饭菜凉了,吴管家又让厨师重新加热一遍。
她慢悠悠地喝汤,一边看手机,宗梨来一张照片,两个男人骨骼肌理之间对撞,浑身的劲力满得要溢出屏幕。
一个风清俊朗,骨子里凉薄,也藏着极端病态,似日夜变换云雾猜不透实质到底是黑是白还是灰。
一个清隽谈笑间,深沉内敛骨子底下野性难驯。
宗梨:「到目前为止,我只给你,问就是没测出来。」
客厅里,杨医生正在给徐沉渊检查换药,“徐二公子得罪姑娘了?”
徐沉渊淡淡睥他,没吭声。
说不给她咬哪里肯听,她不消气,他也添堵。
在不给吸烟上基础上,又加了一条不给受伤,从欠她的‘不能说谎’三个问题变四个了。
杨医生取出创伤药,眼神轻眯,视线太子爷落在野性难驯裸露上半身,一道道爪印,吻痕,牙印,见了红。
又不经意看向喝汤的那位,娇俏,纤廋,过程太激烈顶不住刮也正常,还别说,太子爷这幅样子挺糜艳。
这姑娘,他两年前见过,徐二果真带回家了。
他向来眼尖,“小夫人,我这药膏是独家秘制,对类型的伤口好得快,没过久又能刮能咬了,要不要来上几盒。”
温桥舀了一勺热汤放嘴里,又痒又呛汤汁在喉间蔓延,险些喷了出来。
她没说话,把问题丢给徐沉渊。
他问,“一件有多少盒?”
温桥轻咳。
她觉得伤药大多通用,不是非得指定这一种,这杨医生就是纯忽悠,但想想徐沉渊又怎么可能不知道。
“1o盒。”
温桥垂眸,有一勺没一勺的舀汤汁儿,
杨医生眉开眼笑,“好咧。”
徐沉渊催她,“温桥,上楼拿现金。”
“拿多少?”
那杨医生举止食指举起一个“1”。
客厅里,杨医生伸出双手,都以为她拿是卡,没深想。
徐沉渊将浴袍随意披上,“改口费。”
她耳根红得像郁金香的花瓣尖尖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