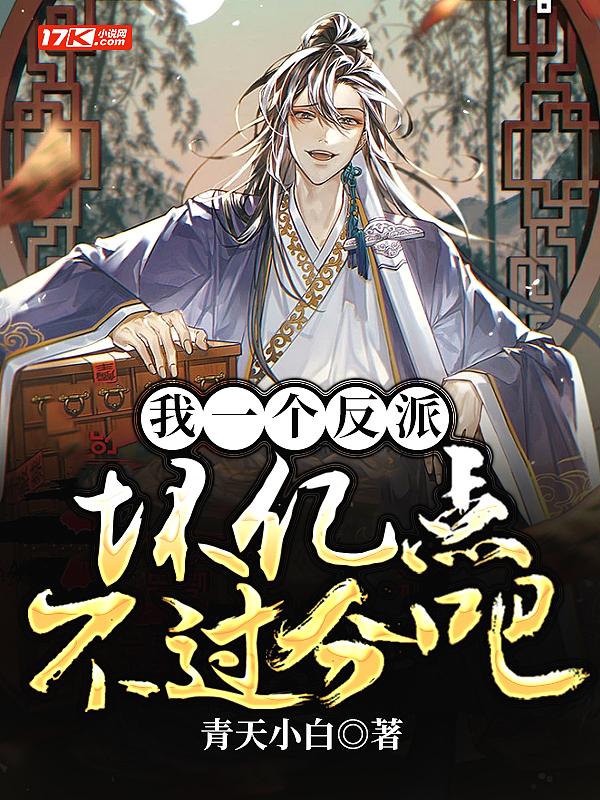言情阁>昼夜撩火 > 第十四章 笑她傻(第1页)
第十四章 笑她傻(第1页)
徐沉渊指腹反复摩挲着她娇嫩的唇,沉声,用了几分力,“我有没有说人情债我来还,不许跟他出去吃饭?”
他的门庭高阁就摆在那,权力、地位、经济。
哪怕一个多月来不联系,也要本能地骨子里大男子主义的控制欲,来管控她的社交。
他的温柔多情,又懂得大把烧钱给女人制造浪漫,有的是美人愿意润物细无声地轻哄着。
阶级高,能轻易给予得多的徐二公子,自然而然获得掌控权,毋庸置疑的。
温桥一把将大片精贵黑衬衫撑开,敞露出嶙峋的,臌胀的胸廓。
温软的两只碧藕穿过劲廋有力胯骨、后腰、肩背。
沟壑起伏分明,有韧劲有弹性的肌理,力量感蛰伏其中。
夜凉,似滚烫火炉,引诱人犯。
确定了,外面那一层黏黏糊糊的都是旁人的血。
挺可笑,如此庞大的商业布局、谋局,又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徐家怎么会让徐二公子受伤。
温桥后退边哽咽,哽咽到干咳、喘不上气。
泪模糊视线,就是这幅深隽的眉骨,骨相比皮相更浓,越品越烈,入肺入心。
她的白绒外套,手上都不知沾着谁的血液,更不知有什么东西能让她现在擦眼泪。
轻声说,“徐二公子,很晚了,我回去睡觉了。”
徐沉渊墨色衬衫敞开,阔步上前搂着她的肩,抚着她的柔润背顺气。
“拿纸巾。”
那张哭得苦苦的娇俏脸蛋。
他懂,一句‘徐二公子’开口他就知道她在气头上。
比如,她开心时会直呼姓名‘徐沉渊’。
再比如,她讨哄的时会喊他“徐先生”“先生”。
男人接过陈特助手里的纸巾,那双狐狸眼泪怎么都不断线的,烦闷的躁意涌上心头。
低颈,额头相抵,“温桥,想要什么?嗯?我给。”
他好像在说,我都给颗糖给你了,不要闹了。
他大概是习惯用权力解决事情,没有心的。
只是她的野心很大,很贪心,她什么都想要,他的人,他的心,他的情,他的权,他的贪嗔痴……她全都要。
温桥哭着就笑了。
挣脱他,光影下,可怜巴巴的身影如幼兽,一步步后退。
“没有第三第四次了,林小姐和徐二公子很般配,你若是想娶,徐家阻碍得了你吗?别再折腾旁人了。”
直接戳破其实很蠢的,一点都不大女主。
徐沉渊不喜欢,更不会因为谁去改变,哪怕是说出来也不会改变,哪怕是现在哄、跟她道歉都不会去改变,提了还会让他不舒服,甚至厌烦。
知道让男人付出的底层逻辑就得先把他哄舒服。
但心底那点情绪欲望作祟想知道,挺作。
杪冬的庭院下,八角灯模糊的光晕散开,徐沉渊肩阔挺立隐匿在光斑里,安静听她说完,肃冷的风将精贵的墨色衬衫刮臌胀,指尖的一支烟燃了半截。
缭绕薄蓝的青烟散于眉骨,窥探不到半分情绪。
轻声唤她,“温桥。”
他的嗓音低沉沙哑,像是在轻叹,她听出了缱绻的意味。
徐沉渊一定觉得她是在故意闹脾气,他的耐心就快要完。
三年前也作,三年后还是一样作。
她想,大概是相遇时太惊艳,让她成为最特别的那一个,让徐沉渊忍了一次又一次。
娇俏的身姿后退转身,再次做心理斗争。
“不用转头哄一边,转头还再去哄另外一边,您再也不用去平衡。”
“就这样吧。”
“回去了,深夜,不吵旁人休息。”
陈特助抬头望望这今晚的月色,天道好轮回啊,一物降一物。
他甚至在想,给徐先生划上一道伤痕,也许温小姐就把徐先生带回家了,哪有那么多事。